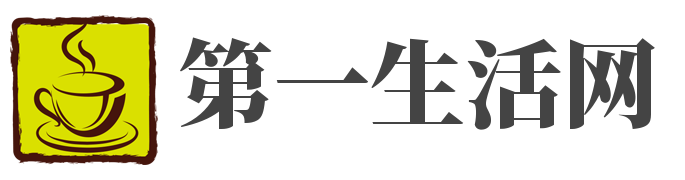我们是不是把孩子逼得太紧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许多父母难以回答的问题。

养育子女一直是一种平衡行为,试图鼓励孩子成功,而不是在压力下屈服。近年来,青少年一直在与惊人的焦虑和抑郁率作斗争,让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孩子的福祉。
那么父母应该受到责备吗?94岁的获奖记者詹妮弗·布雷尼·华莱士(Jennifer Breheny Wallace)说,不完全是这样,她最近出版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永远不够:当成就文化变得有毒——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她的书中,她谈到了当今青少年面临的成功压力。这可能来自父母,他们是更广泛的文化焦虑的渠道,例如全球主义和经济转型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就业市场竞争力。但父母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学生在学校、各种活动以及与同龄人和各种其他人的互动中遇到压力。
Breheny Wallace在接受《公报》采访时谈到了她在研究中的发现,并为父母提供了有关如何为孩子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的建议。为了清晰和长度,对这次采访进行了编辑。
宪报:你从高中三年级的莫莉开始写这本书。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她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Breheny Wallace:她最吸引人的是,她把自己表现得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学生。她分享说,她的许多朋友会在凌晨3点上床睡觉,或者在凌晨3点醒来,所以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她告诉我,因为她不是一个夜行者,所以她在午夜睡觉,大多数晚上,然后在早上5点再次起床完成工作,去体育练习。
我说:“你是一名大学运动员。你是怎么做到的?再一次,没有任何讽刺意味,她说,“是的,我只是闭着眼睛进行练习。好像这很正常。这就是学生的做法,令我震惊的是,她根本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她内化了这些期望,她正在践行这些期望。
宪报:你的书强调了像莫莉这样的学生在进入所谓的“高成就学校”时面临的压力,这些学校往往竞争非常激烈,标准化考试成绩很高。你为什么决定关注这个人群?
Breheny Wallace:正如你所指出的,是的,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来自家庭收入最高的25%。根据你住的地方,家庭年收入约为 130,000 美元。这可能是一个父母都是老师的家庭;我们不是在谈论1%。我们谈论的是中上层家庭。
2019年,我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关于两份国家政策报告的文章,这些报告发现这些学生正式成为高危人群,这意味着他们患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障碍的临床水平的可能性是美国普通青少年的两到六倍。这感觉非常违反直觉,因为得到这么多机会的孩子在切实的幸福感衡量方面做得不如中产阶级同龄人。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全国所有的孩子身上。
这种“永远不够”的感觉随处可见。我并不是说应该从其他人口统计数据中转移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家长和学校资源充足,有能力提供必要的东西来帮助他们的孩子。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痛苦和同理心不是零和的。正如一位研究人员对我说的那样,“没有孩子会选择自己的环境。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此做点什么。
宪报:这本书谈了很多关于成就压力的问题,这导致了这种“永远不够”的感觉。它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它对年轻人的影响?
Breheny Wallace:需要明确的是,我不反对成就。我自己雄心勃勃,我从成就中获得了很多快乐;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这种快乐。成就变得有毒的地方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我意识和价值与我们的成就纠缠在一起时。当你必须实现才能重要时。
今天的学生感受到了这种成就压力,他们从各个方面感受到了压力:来自只想为孩子最好的东西的父母;来自承受着自身压力以达到某些标准的教师;以及承受自身表现压力的公立和私立学校。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压力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们有一种毁灭性的孤独、焦虑、抑郁和自杀流行病;我们看到的一代人正在被压垮。
宪报:关于成就压力的一个误解是,它来自父母将成功置于孩子的幸福之上,或者父母试图通过孩子间接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Breheny Wallace: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真的厌倦了今天的父母只想在汽车后座上贴上标志的说法。我不买它。这种成就压力的根源要深得多。我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交谈,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趋势,但真正引起我共鸣的是当今父母的宏观经济力量。
当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长大时,生活通常在各个方面都更实惠:住房,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甚至我们的食物。我的父母可以相对放心,就像过去几代人一样,即使有一些错误的举动,我也可以复制我的童年,如果不能做得更好。
但今天的父母面临着不同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代人的表现不如他们的父母。他们背负着债务。他们买不起房地产;医疗保健法案正在使人破产。因此,父母感受到了现在我们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深刻的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挤压和全球化带来的超级竞争。
用研究人员的话说,我们正在成为这些宏观经济力量的社会渠道。我们正在以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将这种未知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感觉到对孩子的保障越来越少,我们觉得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编织个性化的安全网。虽然抚养下一代一直是父母的工作,但从未感到如此令人担忧。
宪报:你有什么例子吗?
Breheny Wallace: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对全国6,500名家长进行了自己的育儿调查。我问家长们对这种说法有多大同意或不同意:“我觉得对孩子的成就和成功负责。百分之七十五的父母表示他们有点或强烈同意。
然后我问他们有多同意这种说法:“其他人认为我孩子的学业成功反映了我的养育方式。百分之八十三的父母强烈或有点同意这一说法。
然后我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今天的童年对我的孩子来说压力不大。87%的家长同意或强烈同意。
宪报:您和我们的许多读者都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您是否注意到您的经历与当今青少年的经历之间的相似或不同?
Breheny Wallace:我惊讶于我的经历与我采访的学生如此不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成就对我的家庭很重要。但它并没有定义我的生活。这与我与家人和大家庭的关系一样重要。是的,我的辩论赛很重要。但与我的祖父母和我的叔叔阿姨共度时光也是如此。我有一个健康、平衡的童年,我的自我意识不是由我的成就来定义的。
用HGSE和肯尼迪学院讲师理查德·魏斯伯德(Richard Weissbourd)的话来说,让关怀变得普遍,父母有时将大学视为不确定性海洋中的救生衣。家长们越来越关注大学品牌和声望,希望只要穿上那件名牌大学救生衣就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无论他们将来遇到什么。
但不幸的是,我在研究中发现,救生衣正在成为铅背心,淹没了许多我们试图保护的孩子。作为父母,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策略。重要的不是大学的声望;这是学生如何融入他们的环境并以有意义的方式感到受到重视。
宪报:作为父母,您如何让您的孩子达到高标准,而不会给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以致损害他们的福祉?
Breheny Wallace:这是我从Suniya Luthar那里学到的教训,她在去世前是世界领先的弹性研究人员之一。她说,今天的学生已经充满了关于课堂上的表现的信息,他们的同龄人,老师,大学,社交媒体和更大的文化。他们日复一日地听到他们必须努力的信息;他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且他们只和他们的下一个成就一样好。因此,家需要成为摆脱这种压力的避风港,我们的孩子可以恢复,他们的价值永远不会受到质疑。